國家翻譯隊伍里的外國學者們
作者:黃友義
他們是一批特殊的群體,如果留在自己的國家,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也可能在他們各自的領域里事業有成,成績輝煌;也可能早已腰包鼓鼓,甚至高官厚祿;也可能一輩子碌碌無為。無論如何,那樣的話,他們將與中國無緣,人生變得平淡無奇。然而,中譯外這片廣闊的田野里,有了他們,就如同增添了及時的甘露,開出的花朵更加絢麗多彩,果實更加豐碩高產。耕耘中,他們也成全了自己的事業,收獲了中國人的高度尊重,甚至無限的懷念。這是一支強大的智慧力量,是橫跨數十年的文字大軍。我有機會跟他們當中少數人相識,一道工作,頗為榮幸。在此,給大家介紹其中幾位。
索爾·艾德勒(Solomon Adler)

在我心目中,索爾·艾德勒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1941年他被派到美國駐華使館工作,任務之一是負責協調美國援助國民黨事宜。目睹國民黨官員在獲取美援方面中飽私囊,貪得無厭的高度腐敗,他堅定地相信,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然贏得勝利。因為他的政治立場,1946年被撤職回到美國。作為一名左翼人士,在美國很難有合適的工作。艾德勒先是去了英國,后來來到了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參與新中國建設的各項工作中,我聽人們談到最多的是他參與了《毛選》四卷的翻譯潤色工作。可惜年代久遠,加之當年只顧聽,沒有記錄下來,那些中國的老翻譯們經常舉到的艾德勒翻譯《毛選》的例子我已經無法詳述,總的感覺就是,當大家在翻譯時遇到一個英文詞匯或者句子爭論不休的時候,似乎都依靠他一錘定音。
因為1949年前后他的所作所為,美國政府一度視他為國家的叛徒,他也長期無法回美國探望親人,直到尼克松訪華后,根據兩國的協議,他才有機會回到離別十幾年的美國探親。他的夫人帕特·艾德勒是英國籍,入境美國時,被美國有關部門關在海關折騰了一整天。艾德勒上個世紀80年代因病去世,但是在老一輩翻譯家那里,他的名字經常被人提起。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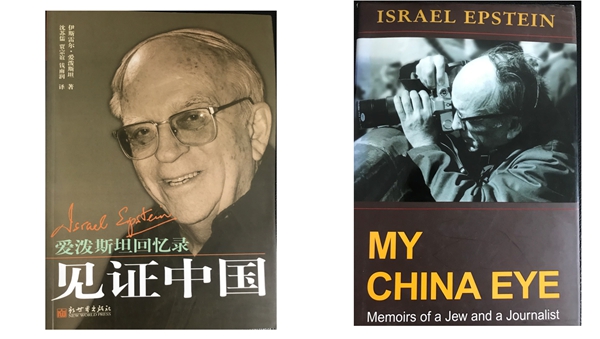
第一次跟愛潑斯坦面對面是1975年在他的辦公室里。我剛剛參加翻譯工作不久,按照工作流程,要把我翻譯的一篇稿件送給他修改。沒多會兒,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給我講述他的修改。我的稿件是用老式Underwood牌英文打字機打出來的,double space專供別人修改。我只記得原來的白紙黑字返還回來時幾乎滿篇紅色,用詞不當,句子順序不暢,更別提信達雅。文章的標題我早已經忘記,應該是關于中國革命戰爭時期的內容,時至今日我只記得他在稿件上寫的一個詞是sanguinary。就是那一天跟他學習了bloody和sanguinary的區別。我用的是bloody,回憶起來顯然太過于口語化了,與文章風格不符,他改成了sanguinary,在那之前,我還根本不知道這個詞。這是我第一次接受他手把手的幫助。
在辦公室大家都稱呼他Eppie(艾培),我把他看成良師益友,倒不是因為他負責修改我的譯稿,而是從那以后幾十年的交往中,我不斷地從他身上獲取智慧和力量。艾培是記者出身,當年作為記者曾經到延安采訪,1951年他從英國來到北京參與創辦《中國建設》雜志,1979年擔任了總編輯。他一生中,采訪和寫作的時間超過修改譯文的時間。早在1947年就在美國出版《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一書。我第一次去他家,是1975年他從西藏采訪回來,喝著他帶回來的酥油茶,聽他介紹采訪見聞。為了準確地對外介紹西藏,他曾經四次赴藏,其中《西藏的變遷》成為西藏民主改革后第一本由外國人直接撰寫的專著,在國外影響很大。無論是擔任一般的改稿專家還是雜志總編輯,艾培對中國翻譯尤其是年輕翻譯的幫助不僅僅在于學會幾個英文表述,而是從根本上意識到這樣一個理念,用他的話說就是外國讀者都是大學水平,但是對中國的認知僅僅是小學水平,給外國人看的文章、圖書必須考慮外國人對中國的認知程度。
跟艾培相識30年里,見面次數很多,聽到他最多的問話就是What are you working on? 30年間從來沒有聽到他為了自己的待遇和生活提出任何一個問題。在他的晚年,唯一一次打電話找我不是談書稿和翻譯人才培養問題,是讓我幫他找一位熟悉電腦操作的年輕人到他家處理電腦故障。一生中,他寫中國,講中國,在國內接待外國來訪者和到國外參加會議、探親也都會介紹中國。然而,他自己的傳記《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在美國就是找不到主流出版商。多家看過他稿件的外國出版社都表示個人經歷非凡,書稿引人入勝,但是不增加對中國的批判就無法接受。當然,艾培絕對不可能接受外國出版商的意見。最終,該書的美國英文版是由外文局在美國設立的長河出版社出版的。艾培一生致力于傳播中國,培養中國對外翻譯專業人才,贏得了同事的高度尊重,也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充分肯定。在他80周歲時,江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他;他90歲那年已經坐上了輪椅,胡總書記親自到他家看望他。這兩次都由我在場翻譯。記得胡總書記一落座,就談起閱讀艾培回憶錄的感想,也一下子把艾培帶回到了在延安的日子。他指著攝影記者、在延安出生的周幼馬(艾培老友馬海德的兒子)說,在延安,那時我抱著他,現在他抱著我(指從床上搬到輪椅上)。令人寬慰的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設立了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研究中心,他豐富獨特的外宣理念得以傳承。
沙博理(Sidney Shapi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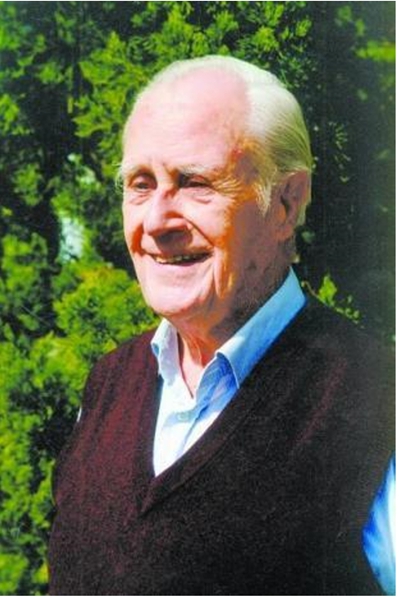
我們都稱呼他老沙。他1915年出生在美國,1947年來到中國,2014年在99歲高齡時在北京去世。有人記得他,是因為他翻譯過《水滸傳》,有人把他譽為“紅色經典翻譯家”,因為他比任何一個人翻譯的近當代小說都多,包括《新兒女英雄傳》《保衛延安》《創業史》《林海雪原》《月芽》,還有經典作品《家》《春蠶》《李有才板話》《小城春秋》《孫犁小說選》《我的父親鄧小平》《鄧小平文革十年》等著作。沙博理還著有《我的中國》《四川的經濟改革》《中國封建社會的刑法》《中國學者研究古代中國的猶太人》《馬海德傳》等。他還出演過三部電影《停戰以后》《長空雄鷹》《西安事變》。
沙博理一生中獲得多個獎項,去世前不久剛剛獲得“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他能獲得這個獎項還有一段故事。“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是一個鼓勵中國圖書對外傳播的政府獎勵項目,每年頒發一次,獎勵那些在國際上寫中國的作家、翻譯中國圖書的翻譯家和出版中國著作的出版家。從2005年開始,已經舉辦了13屆,《狼圖騰》英文譯者美國人葛浩文就是第四屆的獲獎者之一。沙博理在獲獎提名人員當中頗有競爭力,因為他不僅翻譯中國,還寫作中國,作為長期在外文局工作的語言專家,他還是對外出版隊伍里重要的一員,也算是從事出版中國,“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三類獎勵對象選他一個人都占全了,這是多年參加評獎的人員里絕無僅有的。2014年他終于進入獲獎終審名單,但在審查他的具體條件細節時突然發現他早已加入中國國籍,而評獎條件里明確規定這項獎勵頒給外國人。鑒于他的情況特殊,主持評審工作的領導決定暫時休會,等大家再回到會場時決定先討論是否需要修改評審條件。那天的結果是評委們決定把評審條件中外國人的規定改為包括加入了中國籍的外裔人士,沙博理全票獲得該獎項。這樣做的理由很充分,作為一個開放的大國,中國也還會收到外國人的入籍申請,也許將來某一年又有漢學家申請入籍。不能因此把這部分特殊群體排除在獲獎人選之外。
沙博理翻譯的最后一本書是《鄧小平文革歲月》。雖然文革期間他就生活在北京,但是畢竟和普通中國人不一樣,他沒有深深地卷入政治派系斗爭,書中許多涉及文革的細節他還不十分清楚,就把我叫到他的家里,他向我了解當時的社會情況,我則看他如何處理各種表述,向他學習翻譯。再后來,因為年事已高,他不再翻譯,但是仍積極參加全國政協的活動,出席各種會議,包括到國外論壇上介紹中國。即使后來不再遠行,也通過寫文章和跟外國人通信來介紹中國。
他時不時通過郵件發一兩個英文笑話,跟朋友們輕松一刻。遠在人們講段子形成風氣之前,我從沙博理那里聽來了許多美國的笑話,多數是調侃美國律師的,可見美國人對律師又愛又恨,而對我,既學習了英文,又了解了美國社會。
他始終保持著快樂、睿智的精神狀態,熱愛生活。他的生日是12月23日,我們經常要征求他的意見,到哪個飯館給他慶祝生日。他也常常拿著中國日報上介紹的新開張的西餐館作為生日聚會的地點。他越是年長,我們對他的稱呼也變得越是年輕,以至于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我們許多人都稱呼他為“young man”。然而自然規律無法抗拒。到后來,老沙不止一次托人帶話讓我去他家,我原來以為他有什么事情要說,后來發現,他讓我坐在他的身邊,我們只是默默地坐著,他已經沒有了往日交談的興致和精神,不由令人傷感。
2014年他的去世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至今沒有任何一位出生在海外的外國人或者中國人在翻譯紅色經典作品方面能夠與他相比。
戴乃迭(Gladys Yang)

很多人有一種印象,似乎戴乃迭的作用就是潤色其丈夫楊憲益先生的譯文,其實她獨立完成的譯文也很多。有一次,我就聽她給我們講述她翻譯民間故事《阿詩瑪》的經驗。她說道,翻譯要想到讀者的閱讀感。比如阿詩瑪的名字按照漢語拼音應該是Ashima,但是這樣英國讀者發音會很困難,所以她果斷地把名字改為Ashma,使之更容易上口,也讓這個人物更加親近。
我的記憶中,戴乃迭高高的個子,炯炯有神的眼睛。無論是在辦公樓里見到她,還是在大院里看到她帶著自己的外孫玩,還是在她家里聊天,她永遠給人一種典雅而又可親的感覺,總保持一種與眾不同但又平靜如水的神態。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在中國的街頭巷尾很少能見到外國的小孩。在外文局的大院里,我聽到戴乃迭的一個外孫說另外一個孩子:You are being very naughty! 小大人一般的孩子,標準的英式英語,我當時想,這句話一定是孩子從外婆那里學來的。
陳必第(Betty Chandler)

來自美國俄勒岡州的美國人,1937年來到嶺南大學學習,1959年到外文局工作。她在改譯稿時不留情面,敢于大幅度修改,一筆英文字,十分漂亮。上個世紀80年代初,出版社發現教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教材品種太少,領導安排陳必第和我編寫一個漢語口語小冊子,后來以《學說中國話》為題出版。教材的編寫過程基本是她寫英文,我給配上漢語拼音和漢字。不僅跟她學習英文表達方式,還學到了其他知識。那是一個人們生活還非常清貧的時代,我們理發通常都是親戚同事之間互相幫忙,很多單位的辦公室里都有公用的推子,當然那時還是手動的。自然,我對正規高檔理發店里的服務流程根本不了解,更不要說涉及到女性的頭發護理。陳必第寫了一句英文 I want a shampoo and set. 每個英文詞我都熟悉,但是因為知識面的欠缺,我不知道set用中文怎么說。她脫口而出:“做頭發。”說實話,此前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做頭發”。那是一個不講究作者和譯者署名的時代,出版時領導決定那本書的作者署名為“程荒”,分別代表陳必第和我二人。
許多外國人在其學術生涯的某個或者某幾個階段來到外文局,參與翻譯、編輯,包括譯稿潤色的工作,成為國家對外翻譯和出版事業的參與者。
羅慕士(Moss Roberts)

羅慕士1966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博士學位,兩年后到美國紐約大學教書,一直到現在。雖然已經80多歲高齡,仍然孜孜不倦地講著《三國演義》的故事。他研究三國,閱讀三國,教授三國,當然也翻譯三國,且翻譯了不同版本介紹三國的書籍。當然,其中最為著名的是1991年在美國和中國同時出版的英文版《三國演義》。在動手翻譯《三國演義》全本之前,他已經翻譯了節譯本,于1976年在美國出版,成為大學讀物。1983年到1984年他來到北京專職翻譯《三國演義》。外文出版社為此特意給他安排了老翻譯家任家楨配合他的翻譯工作。羅慕士自己曾這樣說:“任先生認真細致地校對了全部譯稿,并與我分享他的學識和經驗,他的建議極大地提高了譯文質量。”
詹納爾(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
詹納爾1962年畢業于牛津大學,算起來應該是戴乃迭的校友,只不過戴乃迭1940年在重慶與楊憲益結婚時,詹納爾才剛剛出生。人們提起他,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紀80年代他完成了《西游記》的翻譯。其實,早在1963年到1965年期間,他就在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完成了溥儀傳記《我的前半生》的翻譯。據他本人回憶,當時出于對英文版權的保護,中文版一邊籌備出版,英文版一邊翻譯,憑借扎實的功底和出版社提供的各種便利條件,他很快完成了這部作品的翻譯。若干年后,意大利電影導演拍攝《末代皇帝》,就是購買的這本書的英文版權。此外,詹納爾還翻譯了《魯迅詩選》等圖書。
在一篇題為“東游記”的回憶性文章里,他說12歲的時候,偶然讀到了亞瑟·威利翻譯的《美猴王》,從此與孫大圣結下不解之緣。《西游記》的翻譯實際上是他1965年在外文社工作時開始的。后來,他回到英國到利茲大學任教,趕上文革動亂,出版社也無暇顧及他的翻譯,直到13年之后的1978年,外文出版社再次聯系他,催促他完成翻譯。他找到已經翻譯了三分之一的書稿,修改完善,并于1979年回到在外文出版社他曾經工作的辦公室繼續翻譯,以后若干年,他利用假期年年回到北京,集中精力完成翻譯,直到1986年全書最終出版。翻譯《西游記》他特別在意讀者的閱讀感受。可以想象,把一部基于中國文化,有著大量佛教和道教色彩的民間傳說性作品翻譯給文化和宗教背景完全不同的英文讀者,其難度之大,幾乎可以與玄奘西行取經相比。在這種情況下,譯文的流暢遠遠高于學術上的闡釋。確定了英文讀者能夠得到跟中文讀者同樣的快樂這一目標,詹納爾放手發揮。他不再看亞瑟·威利的《美猴王》,為的是不重復前者的表述,同時也不刻意回避使用相同的表述。他尤其看重《西游記》的敘述方式與其他歷史名著不同,更像是講故事。他的譯文追求給讀者帶來娛樂,而不是把譯文變成生澀的學術研究硬塞給讀者。在他看來,故事比語言重要。受眾需要記住的是故事情節而不是英語語言。語言不能太現代,因為原著完成于幾百年前的明代。英文要大眾化泛區域化,不能讀起來給人一種好像故事發生在某一個具體的英語國家的感覺。四個人物的語言要與各自的性格相匹配,不能都講玄奘的一種語言。他追求的目標是語言順暢輕松以至于讓讀者感受不到是在閱讀一部譯著。為此,他必須調整句子結構,做必要的刪節。他特別注意不要為了說明一些佛教和道教的概念,時不時出現學術思想的解釋,干擾讀者享受故事。
他在北京翻譯《西游記》期間,我經常有機會跟他見面,遇到翻譯上的各種問題,經常向他請教。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翻譯們遇到問題需要請教不外乎三個渠道:一是查看大英百科全書;二是打電話或寫信向專家請教,比如我翻譯考古文章時,就向社科院的考古專家或者文物局的專家請教;三是最多也最為方便的,就是向同一個部門的外國人和老專家請教。說起來慚愧,有一次我向詹納爾請教一個詞匯如何翻譯成英文為好,他首先糾正我對一個漢字的讀音。一方面說明我的中文功底不牢,另一方面說明了他中文的老道,不得不服。
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

杜博妮是一位成名早、作品多、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齊頭并進的漢學家。她1980年到1983年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時,任務之一是翻譯《兩地書》。那時,她剛剛完成《何其芳詩選》的翻譯。她的主要工作還包括修改中國譯者的各類翻譯稿件,但翻譯《兩地書》已經成為她的主攻方向。作為一位認真的學者和翻譯家,在翻譯這本書時,她對魯迅和許廣平的生平做了深入了解,其中一次是到魯迅博物館參觀座談。那天我陪她去魯迅博物館,座談時她準備之充分,背景了解之詳實,令我非常驚嘆。后來,我才知道她此前通過信件跟《兩地書研究》的作者、館長王得后聯系過,使這次座談非常深入細致,為她更好地把握翻譯環節起了很大作用。
杜博妮是澳大利亞人,她的丈夫韓安德是瑞典人,也是一位漢學家。杜博妮雖然已經退休,但還是經常參加漢學會議,到中國參加文學翻譯活動。韓安德近年則一直參加“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翻譯和潤色。
薩拉·格拉姆斯(Sara Grimes)
美國人格拉姆斯是報社記者出身,后來從事新聞教育,上世紀80年代初期來中國前是美國麻州大學新聞系教授。當時她不會中文,主要從事英譯文的改稿。但是,記者的功底讓她在潤色稿件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我們也都知道,如果我們的譯文過不了她改稿這一關,一定是我們的表述有問題。當時為了滿足日益增多的外國游客的需求,外文出版社決定翻譯出版《西湖攬勝》一書的英文版和日文版。因為文化接近,日本版譯文交給日本語言專家后,很快修改完畢付印出版,英文版的譯稿交給格拉姆斯后,她發現英文讀者看不懂的地方超過能夠看懂的地方,而西方游客需要的內容書里又沒有提供。要讓一本中國學者本來寫給中國讀者的書稿適合歐美游客的口味很難。于是,出版社領導決定發揮格拉姆斯采訪撰稿的本領,派她到杭州實地采訪調研,然后改寫這本圖書。我的任務是陪同她采訪。一路上當地學者詳細介紹每個景點以及背后的人文故事,格拉姆斯邊聽、邊看、邊在本子上記錄。晚上把采訪記錄打成文字稿,交給我核對。兩天下來,我發現她的記錄詳盡準確,然而這都是邊走邊記的,很多時候是爬著臺階做記錄的。出于好奇,我也試著邊走邊看邊記錄,結果是我無法認識自己的記錄,更不要說她那種規矩干凈的記錄了。顯然,這種功夫不是短期就可以練就的。
從杭州歸來兩周后,她拿出了完整的書稿,基本上保留原作的框架和風格,但是在表述上完全站到了向外國游客介紹西湖文化和風景的角度,沒有了此前西方讀者感到晦澀深奧的不知所云,取而代之的是對一個美輪美奐令人向往的地方的描述。新書出版,銷路暢通,浙江的同事最為滿意。兩年后,格拉姆斯回到麻州大學,申請終身教授資格,展示的作品就是英文版《西湖攬勝》。她的努力幫助成就了這本介紹西湖的英文圖書,而這本書也成就了她終身教授的事業。
平克姆(Joan Pinkham)

很多中國譯者認識平克姆是閱讀過她的《中式英語之鑒》一書,我認識她是因為她作為外文出版社的英語專家修改我的譯文,她也是有生以來對我批評最厲害的外國語言專家,但是這次痛斥讓我徹底懂得了沒有搞懂原文,就不要翻譯的根本道理。上個世紀70年代,中科院組織專家對青藏高原進行了大規模的科學考察,我參加了《青藏科考》一書的翻譯。圖書內容專業性很強,涉及多種學科,翻譯難度可想而知。一天,她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拿著她正在修改的我的譯稿,向我提了幾個問題,我的回答令她很不滿意。她問的問題都是關于高原科考專業的,而我對許多科學理念根本沒有搞明白,就照字面翻譯,顯然,話說不清楚,邏輯表達混亂。她突然提高嗓音說:“既然你沒搞懂,為什么要翻譯?!告訴你,我翻譯的原則就是沒搞明白,絕對不動手翻譯。”雖然,她的語氣很嚴厲,但是講的是真知灼見,既是經驗之談,也是她長期在美國從事翻譯工作的深刻體會,何況她歷來說話直率,干凈利索,從不拖泥帶水。她說話如此,譯文也是如此。經過這次振聾發聵般的談話,不搞懂原文的意思,不要翻譯,從此成為我遵循的原則。
較真是平克姆的特點,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她把參加《鄧小平文選》等中央文獻譯文潤色工作中發現的問題,集中整理后編寫了《中式英語之鑒》。作為一名美國的英法互譯職業翻譯,她對中譯外的實踐和人才培養做出了特有的貢獻。
這幾位參加中國對外翻譯和出版的外國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以愛潑斯坦為代表,他們先后參加了中國的革命,后來加入了中國國籍,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他們不僅是最初的訪客,也在中國革命最需要的時候毅然加入中國的外宣隊伍,是跟我們志同道合的新中國建設者。很難想像,當年面對西方的封鎖,沒有他們的參與,我們的對外翻譯會是多么困難。在對外出版方面他們的意見一向得到高度重視。比如愛潑斯坦曾經提出,把1949年之前外國人寫中國的圖書整理重新出版,一是幫助外國讀者認識歷史,二是填補對外圖書品種的不足。這個建議得到朱镕基總理的批準,國家撥專款出版了一整套名為“中國之光”的外國人寫中國系列叢書。沙博理更是希望與中國同事不僅同一個辦公室工作,還要“同吃同住同勞動”。1977-78年我在五七干校勞動,就跟他在一起朝夕相處過一段時光。由于他在,自然在干校里凝聚了一批外語專業人員幾乎天天晚上在一起聽英文廣播,談論中外關系,切磋對外翻譯,探討對外出版。
另一類跟中國翻譯出版結緣的外國學者又分為兩個小類別,一類是漢學家,他們一生都在通過翻譯、寫作和教書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如羅慕士、詹納爾、杜博妮。還有一部分人并不是學習中文出身,但是出于對中國的好感和好奇,拿出自己一段時間在中國工作。雖然背景不一樣,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幫助了中國的對外翻譯和文化傳播。同樣,他們都展示了嚴謹的治學態度,執著的職業精神。
當然,由于背景不同,又沒有加入中國籍,他們對我們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在認知上跟愛潑斯坦他們那一代不可同日而語。其實,他們的到來就是一種體現在當代對外翻譯上的文明互鑒。他們用自己的專業幫助了中國,也從這個事業中獲得了自己的成就。與此同時,也讓他們身邊的中國同事零距離了解了外國人的思維模式和文化行為。這對我們從事翻譯是一種鮮活及時的幫助,我們可以從平時接觸中發現彼此的差異和共性,加之日常工作中需要不斷磨合,這大大增加了我們對外國讀者對象的清晰認識。
 0
0 






dc3f2639-0705-44ad-abe2-ca496bde1e52.jpg)